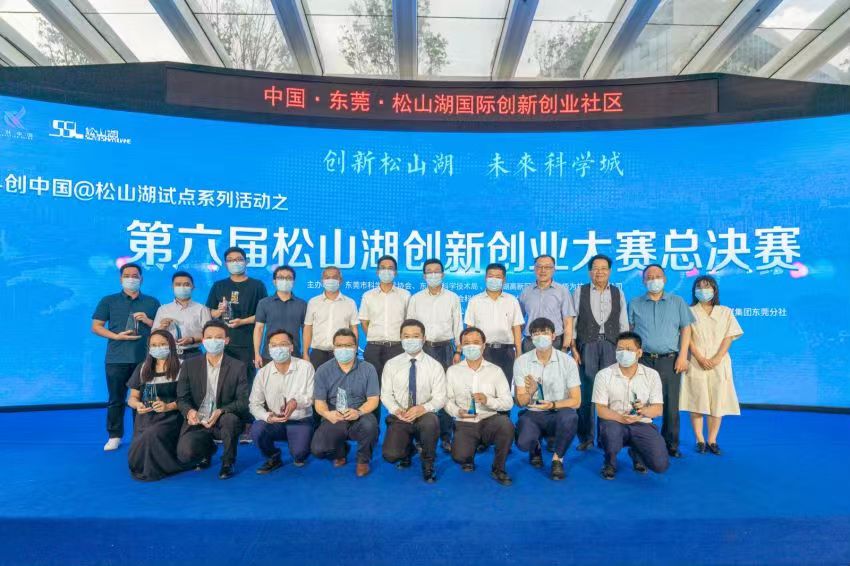凤凰网
7月12日至15日,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新疆考察调研。他强调,要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研究;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,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。
和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相比,“中华民族”这一概念,只有百余年历史。1902年,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中首提“中华民族”一词。“齐,海国也。上古时代,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。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:一曰国家观,二曰世界观。”次年,他发表《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》,初步表达其对中华民族的理解。
“读书穷理,以极其至”。自梁氏提出“中华民族”概念以来,几代学人从多维度探勘,体认识到中华民族具有实体性、包容性、开放性等特质。考古学家夏鼐1962年提出,“各兄弟民族的祖先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,与汉族的祖先建立起日益紧密的关系,今日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”。后来,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基于自身的田野调查经验,根据中国民族发展实际情况,提出“中华民族多元一体”的观点。
十八大之后,“中华民族共同体”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日渐成熟。2014年的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、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、《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》、十九大报告等,都反复强调要培养(铸牢)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。
2022年3月5日,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,既要做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工作,也要做大量‘润物细无声’的事情。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,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,各项工作都要往实里抓、往细里做,要有形、有感、有效”。
由此可见,中国政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与定位是由浅入深、由表及里的深刻演化。
某种意义上讲,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在内涵上并没有本质区别,“共同体”(community,表示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和伦理取向的群体生活方式)仨字貌似有蛇足之嫌。其实不然,在这一语汇中,“共同体”是核心概念,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机的共同体而不是松散的联合体,不是机械式的“马赛克”拼凑,而是56个民族融入于共同体中并依赖共同体而自我完善、互惠共生的状态。
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卓识深意,大致可从历史、文化、国家三个维度来看。中华民族能够合诸民族以成一体,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。各民族均是历史的同行者、参与者、亲历者、书写者和见证者。诚如史学大家吕思勉所言:“一国之民族,不宜过杂,亦不宜过纯。过杂则统理为难,过纯则改进不易。惟我中华,合极错杂之族以成国。”
中华文化由中华民族创造出来,中华民族又由中华文化融凝到一起。共同文化是由各民族在互动交往中共同参与、共同创造、共同守护的,共同文化并非同一的、强制的、挤压的,而是多维的、平等的、共生的。兼收并蓄的特性,能够将人们紧密团结起来,增强共同体的牢固性。
改革开放为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。这几十年里,市场经济活力迸发,各民族的跨区域人口流动频繁,而流动人口往往对新事物更敏锐,进而开发出事物的新功能,发现新的机遇。由此,各民族在推动现代化、共享现代化成果的同时,缔结了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。
“长相知,才能不相疑;不相疑,才能长相知”。戏剧大家曹禺在《王昭君》中写的这段话,蕴含着人与人、民族与民族和谐相处与真诚合作的襟怀。今后,在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,可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:
破解“结构困境”,增强“内生聚合”,推动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。加大对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、产业结构调整支持力度,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。大力补齐民族地区就业、教育、医疗等社会事业发展短板,完善沿边开发开放政策体系。简言之,就是 “饭碗”多起来,“短板”补起来,“底线”托起来……
深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涵,推陈出新,丰富共同文化的内容。近代思想家杨度在《金铁主义说》一文中指出:“中华之名词,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,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,乃为一文化之族名。”这种文化,本身就是一种“共享”“共创”的文化生命体系。在风险时代,中华文化更应继续利用吸收人类一切现代文明成果,并在“走出去”的过程中增进与世界各族文明间的对话。
坚持在法治轨道内管理民族事务,推进边疆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“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,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,民族团结才有保障,民族关系才会牢固。”在实践中,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理,既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刑事问题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,也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矛盾。正所谓 “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,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”。
利民之事,丝发必兴。安民利民怡民,始终是贯穿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价值归宿。“多搞一些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项目,多办一些惠民生的实事,多解决一些各族群众牵肠挂肚的问题”,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继续释放良好预期,把良好预期转化为发展实绩,让实绩与预期同频共振。
责编:翠果
责编:翠果
- 下一篇:2021安徽年度经济人物评选正式启动
- 上一篇:暂无